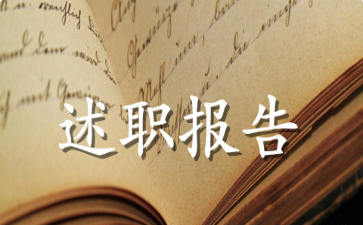罗 峰,蔺若冰,柳雅思,陈红莉,徐雨薇
(1.华中农业大学 农村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0;
2.武汉市武昌区郦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湖北 武汉 430000)
(一)问题提出
伴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发生了急剧变化,社会治理面临较高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传统的社会治理在管理理念、技术、机制等方面逐渐失效,难以有效应对复杂而多样的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政策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城市社区从“建设”向“治理”的转型[1]。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极大凸显了社区在社会治理中的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基层社区的重要性充分肯定:“无论是应对疫情、抢险救灾这样的突发性风险,还是应对日常治理中涌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只有社区基础扎得牢,才能确保无论遇到何种变数,都能做到沉着应对、心中有数。”一时之间政府和社会各界资源大量涌向社区,社区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中流砥柱。然而,如何有效调动这些资源、协调各种社区治理主体真正发挥作用,是当前社区治理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近年来党和政府多次提到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强调社会工作、社会组织、社会福利资源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提倡多主体共治。近五年,不论是基层工作者还是学者,都在此方向上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提出“三社联动”“网格化治理”“参与式治理”等一系列社区治理模式,其共性都在于强调社区内各治理主体的充分互动与协商参与。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视角:
一个是从治理主体的层面,以一个、两个主体为关注点,通过主要的治理主体带动社区整体的多元共治。在这种观点下,一部分学者将目光集中于党建的引领作用[2-3],以基层社区的“红色物业”“红色管家”为切口[4-5],主张通过党建链接社会资源和服务[6],拓宽社区治理网络,再造多方主体之间的连接和关系,向其他治理主体赋权,推动社区治理结构从分散向紧凑转变[4]。另一部分学者聚焦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性:一方面主张在实践层面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公共性与治理动力[7];
另一方面强调在制度层面为社会组织松绑,为其发挥作用、实现自治创造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8]。在此基础上,近年来更多学者倾向采用“嵌入性理论”的框架,来解释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强调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自主性与对话性[9-11]。
另一个视角是从治理技术的层面,创新社区治理的新模式、新机制。不同类型的基层社区所运用的治理技术有其特定的关系结构与运作逻辑,特定治理技术与治理场域的良性互动需要遵循一定的适配逻辑[12]。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部分学者考察网格化管理在社区的实践、可行性以及优势和缺陷[13-14];
部分学者则研究通过“互联网+”社区治理探索建设社区协商互联平台、创新治理机制的可能性[15-16];
还有学者试图整合现有治理技术,探究智慧社区、数字社区实现的可能性[17-18]。
已有的社区治理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总体来看,学者们在阐述从基层社区实践出发提炼出的社区治理模式时还存在以下可以拓展的地方:第一,社区治理主体仍较为单一。尽管强调社区的多元共治,但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对社会组织、党建、居委会等角色的刻画,而缺少居民、社工、志愿者或下沉党员等其他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第二,社区治理主体间协作有待进一步挖掘。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各个治理主体如何行动促进社区治理,而对于不同主体之间如何互动开展协作着墨较少。
(三)案例介绍
武汉市X街道,临江而建,辖区内共15个社区,主要由院落型、新旧混合型小区组成,现有常住人口11.1万,辖区党员4948名,其中流动人口和特殊困难群体较多,因而居民需求广泛且多样化,但各治理主体缺乏连接纽带,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协作能力较弱,社区治理面临较大困难。2019年8月,湖北省民政厅和W区民政局在X街道委托武汉市武昌区郦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实施党建引领“红色社工”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党员、社会工作、社会组织与社区志愿者多个主体合作,从社区治理的多个环节介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探索出“党建引领+五社联动”的“一建五联”社区治理新模式,极大改善了社区治理面貌。
社区从来不乏帮助居民解决困难、提供服务的人,但在党建旗帜鲜明引领社区治理前,社区中的各种主体往往零零散散,各自为战,尽管他们帮助社区解决了许多实实在在的问题,但当社区面临紧急的突发事件,或长期根深蒂固难以化解的问题时,这些各自为战的主体便显得力量微薄。凝共识、聚合力的“党建引领”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
(一)思想引领,凝聚治理共识
在党建引领下,社区治理首要解决的便是思想偏差问题。X街道的Y社区是典型的拆迁还建社区,原来是城中村,社区多拆迁移民,因而人口构成比较复杂,观念和认识上的差异成为社区居民纠纷不断、难以沟通的根本原因。如何能让居民包容差异,合成“一家人”?Y社区开始加大对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主要利用每月“三会一课”的机会,社区工作人员与党员居民建立经常性联系,党委的决策都能够有效落实,党委委员的身份职责更加清晰。同时,普通居民党员思想觉悟显著提高,他们开始从心底里将自己作为社区的一员,作为社区治理和服务的主体,开始为社区做实事,也开始对其他居民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除此之外,X街道各个社区通过“设立驿站”“制度上墙”,加强党建对居民以及各个治理主体的思想引领作用。在“党群服务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下,社区往往会自主建立其他红色驿站,如D社区的“红色驿站”,Y社区的“初心驿站”以及S社区的“红色养老联盟驿站”,这些驿站成为居民开会学习、交流思想、增强信念的重要场所。不仅如此,社区居委会将当前党和政府以及本社区的重点工作、规章制度、治理成效以海报、栏目、宣传册、标签的方式在社区范围加以宣传,让居民知晓。通过这种有形的方式,并以仪式化、场景化的手段增强党建对民众的感召,在观念认同层面凝聚社区共识。
(二)党员示范,聚集治理合力
居民党员在思想上形成统一认识后,通过身体力行和党员号召力带动其他居民主体逐渐、自觉参与到社区服务中。D社区近年推出的系列党建项目就是由下沉党员配合社区工作者一步一步拉出来的成果。2020年初,为关怀疫情后居家老人的心理和身体健康状况,D社区的下沉党员和志愿者组成“一公里”团队上门为老人服务,来自不同行业的党员发挥所长,医生党员为老人做日常身体检查,电气化行业的党员入户为老人检查电路、天然气、水管,部分时间充裕的党员志愿者则将老人推出家门,一起聊天、散步、买菜买药……下沉党员在下沉过程中找到了意义,因而经常带着自己的孩子共同为老人服务,帮老人打扫卫生、走亲戚、陪聊天,社区工作者发现老人很喜欢小孩为他们服务。
老人喜欢讲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有的小孩还蛮喜欢听,小孩朝气蓬勃老人也欢喜。
——D社区书记
在这样的契机下,D社区动员辖区党员、志愿者、青少年、少先队员一起为老人服务,延续红色血脉,从而产生了“红纽带”项目,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的红色“基因”逐步参与到社区服务中来。
社工在我国基层社会普及范围有限,居民认可度相对较低,郦民社工进入X街道后经历了较长的融合过程,从不被居民认同到被热情接纳,从力量单薄、无依无靠到资源丰厚、社群活跃,极大地撬动了社区治理的杠杆,重建了社区连接的纽带。社工在社区治理中是如何“点石成金”的呢?
(一)需求评估者:找准社区治理痛点
X街道既包括院落型小区,也有新旧混合型小区,街道人口构成复杂,居民的年龄层次、经济收入、教育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这也决定了街道内不同社区治理的难点、突破口有所差异。社工介入社区社工服务站后,综合社区的地理位置、人口构成、历史遗留等因素,精准定位治理矛盾。在G社区的橡树湾新型商品房小区,社工认准邻里情感淡薄、纠纷不断的问题根源,以青少年为切入点开展“公益农夫”、中医药科普、健康挑战赛打卡等活动,通过孩子撬动整个家庭,极大促进了邻里关系改善;
在位于插花地的O社区,权责不清、责任推诿问题严重,社工引导三方联动,打造红色物业,明确社区事务责属,社区治理秩序极大改善。
(二)方法指导者:传递专业治理理念
社工进入X街道,将“助人自助”“授人以渔”的专业理念深度推广,使社区各个治理主体从根本上认识到“治理为人”的要义。除此之外,社工运用专业理论,在活动策划、项目组织、效果评估等环节为社区严格把关,从专业角度出发保证社区活动的质量和效果。以G社区“儿童为本”全人教育生态社区的打造为例,社工在儿童发展整体观的视角下,运用“全人教育理论”“认知行为理论”重新认识社区儿童成长的现存问题,综合个案、小组等介入方式,成功打造儿童教育生态圈,由儿童撬动家庭,实现邻里融合。
社工在W区民政局的领导下,经过前期的走访调研,确定在街道层面打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社区层面建立15个社区社工站,打造有社区特色的“红色社工”品牌项目。截至2021年底,郦民社工团队已选派7名专业社工常驻X街道开展专业服务,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化程度实现了跨越式提升。
(三)组织培育者:长出“三头六臂”
为弥补人手有限、资源有限、时间有限的治理短板,社工进入X街道后即加大了培养社会组织的力度。社工联合社区工作人员,在短短三年时间,不断培育社区自组织,形成了“八爪鱼互助帮”“乘风破浪志愿者调节队”“红纽带一家亲”等服务组织。同时引导社区合理运用资源,引进“木兰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创益无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下沉党员、居民志愿者、社工、社会组织极大丰富了社区治理资源,社区治理长出“三头六臂”。
社工为社区治理提供了许多理论和方法方面的指导,但人手短缺,服务难以持续性落地仍旧是社区治理最焦灼的所在。为解决这个问题,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工作人员联合社工,从内外双向培育、购买社会服务组织,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的过程中,逐渐成为处理社区事务、服务社区居民的中流砥柱。
(一)培育社区内社会组织,凝聚生活共同体
居民的问题就是社区的问题,而居民的问题根本来源于居民自身,如若能将居民自组织起来,那么许多问题就可以在组织内部得到解决。沿着这样的思路,X街道G社区发起了“公益农夫项目”,成功解决了随迁老人难以融入城市社区的问题。
G社区辖区内的新型商品房小区——橡树湾建成,购房者多为到武汉做生意、读书、工作而落户的外来年轻人,这些年轻居民移居同时带来了许多帮忙照顾孩子的父母亲。而随迁老人多是来自地县级的农民,相较于年轻人,他们爱好单一、圈子狭小,长时间无法适应城市生活。出于关爱、关心随迁老人的目的,G社区的工作人员与社工一同发起了“公益农夫项目”。项目运作初期,G社区整体统筹,社工通过实地调研测量项目可行性,提供项目制度、合同和其他专业性建议,该小区物业则就地取材,在社区办公楼顶楼的平台,开辟出约500平方米的种植面积,接着社区工作人员号召部分居民党员成立公益农夫志愿者服务队,招募居民参加,实地考察农家乐……该项目有了雏形。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加入,公益农夫志愿者服务队逐渐成熟,居民自己运土、施肥、种植、自费牵水管,甚至在种植地周围修建凉亭、搭建爬藤植物架,供居民休息聊天。项目运作到现在,公益农夫志愿者服务队已经完全发展为自主管理、自我组织的社区型社会组织,它不仅让农村老人融入城市生活,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子,缓解了心理问题,而且将有种植爱好的居民聚集起来,促进了邻里融合。
农村老人其实蛮淳朴,他们只是不熟,熟了以后交流是没得问题的,还会相互帮忙,他们其实只是缺少一个平台,“公益农夫”就是搭建这个平台,也解决农村老人融入城市的问题。
——G社区书记
(二)购买社会型社会组织,引进专业性服务
社区内自主培育的社会组织极大丰富了居民生活,为居民提供了交流和沟通的平台,这使得一部分邻里矛盾得到缓解。在发展社区自组织的基础上,X街道多个社区还利用惠民资金向社会购买社会组织,这一举措使得社区内服务不断走向专业化和细致化。
X街道S社区打造的智慧养老项目是向外购买社会组织的典例。S社区老旧小区较多,因而社区内居民以老年群体为主,其中也包括空巢老人和半失能失智老人,子女外出工作导致这些老人平日里无人照顾,独居在家安全无从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下,S社区对外购买了第三方养老服务组织——众诚颐家,服务社区内老年群体,共同打造了“智慧养老”服务。
在这一项目的运作中,S社区为众诚颐家免费提供一栋公共大楼作为服务用地,其余具体策划、实施、评估事项则全部外包给众诚颐家。众诚颐家成立党支部对应各单位、医院、药品提供方、新华社等九大社会慈善资源,九大资源交叉任职,形成院落小组和联盟团队,通过定期会议机制打造老人服务中心,开展了主要面向社区内老年人群体的多样特色活动。大楼一楼为办公区;
二楼设有社区教育学院,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的书画、模特、舞蹈、管乐、烹饪、红色教育课程;
三楼、四楼为老年人提供全托式服务,针对失能失智老人,开展日常照拂、定期体检、文艺汇演、茶话会等活动;
五楼则设有报告厅,社区内重要活动可以在这里举办。
除了S社区购买第三方社会组织提供的智慧养老项目,其他社区也针对自身需求引入第三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与服务。如G社区为调解邻里矛盾购买了具有法律知识背景的社会组织,为居民提供专业的法律指导和援助;
Y社区引入了W区天行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居民提供专业服务。第三方社会组织逐渐成为社区治理的中坚力量,一方面社会组织可以集中专业优势和工作经验为居民提供服务,提升了社区治理的专业化程度;
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的引入极大减轻了社区工作者的工作压力,避免了专业不对口、“干着急上火”却无法解决困难的问题,推动Y街道社区治理向精准化发展。
2021年7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到:“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显然,“五社联动”将成为未来社区治理的主要努力方向,而X街道在此之前,便已经开始探索五社联动的实现机制。其经验可概括如下。
(一)破解“人少事多”,丰富治理资源
基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牵动着社会发展的脉搏,因而社区日常事务庞杂、琐碎且灵活性较高,但“人少事多”也是社区工作的硬伤,长期阻碍社区治理的纵深发展。X街道“五社联动”首要解决的便是“人”多少的问题。
毛主席说政治就是把人搞得多多的,我现在最大的治理经验就是:我有很多人,很多的时间去处理居民很多的事情。
——Y社区书记
X街道与郦民社工合作,已在2021年完成了对15个社区工作站的打造;
运作并监管147个社区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服务覆盖为老、助残、托育、环境治理、居民调解、社区防疫等不同的服务类型;
共计培育和发展了8支能够深度参与社区治理的志愿服务队伍。随着社区内自管党员、下沉党员、居民志愿者以及社会慈善力量的进驻,X街道社区治理主体不断丰富,力量不断扩充,社区事务管理、社区服务逐渐趋向精准化、专业化。
(二)搭建沟通平台,盘活治理网络
社区、社工、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不同主体逐渐参与到社区治理的实务中,形成庞大的治理网络,那么社区各个治理主体如何实现联动?其关键在于搭建沟通交流平台。一方面,社区利用现有的网络技术,使得社工、居民、下沉党员、居民志愿者能够汇聚于同一交流平台,通过“武汉微邻里”小程序、“三社联动平台”、微信网格群等发布社区公共事务,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提供便民服务信息……这使得治理的需求充分暴露,服务与被服务的距离大大缩短,居民与居民实现“面对面”“心贴心”。另一方面,不同治理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经历了长期的磨合过程,通过不断寻找外力,合力打造“红色业委会”“红色养老”“双网格”等联动平台,党建发挥思想引领作用,社区负责引导和监管,社工提供专业的调研、督导意见,社会组织策划专业性服务,社区志愿者落实、开展服务,不同治理主体发挥所长,各尽其能,形成命运共同体,合力确保社区事务的运转。
我们社区被迫无奈,长期人手不足,我自身没有这个力量,没办法,必须得依靠外力,但是这个外力最后也变成我们的内力,这个外力也会慢慢发展,也会寻找自己的外力,这样就融合成了一个整体,整张网都被盘活了。
——D社区书记
(三)筑牢人本观念,增强居民认同
最看重人,只要有人,有熟人,能协调,一切事情都好解决,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Y社区书记
社区治理联动网如何能够持久迸发活力,使得联动效应长效发挥?一是要完善治理监管机制。通过定期会议制、下沉党员考核制、打卡制、考核制督促各主体行为责任,建立评比激励机制激发各个治理主体的服务热情。二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赋予治理主体主动性。X街道“五社联动”有所成效的原因在于,其认识到社区的问题根源在于人,只有开化人的思想层面的问题,社区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G社区的青少年系列项目,Y社区的乘风破浪调节队,O社区的流动党员办公桌……从根本上都在努力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参与增进居民感情,通过服务获得居民信任,这一治理理念深度挖掘了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居民在参与服务与被服务的过程中体验到了认同感和幸福感,从而延长联动效应,推动社区治理不断向纵深发展。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社区在应对纷繁复杂社会问题时,在治理理念、治理机制及治理技术方面仍面临诸多难题,其中各治理主体缺乏连接纽带、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协作能力较弱等问题较为突出,直接影响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为此,武汉市X街道在社区治理过程中,从社区治理的多个环节介入,探索党员、社会工作、社会组织与社区志愿者多个主体协同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探索出“党建引领+五社联动”的“一建五联”社区治理新模式,即党建发挥思想引领和先锋模范示范作用,社会工作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充当需求评估者、方法指导者和组织培育者,一方面引入专业的社会型社会组织为居民提供特殊服务,另一方面培育社区内自组织实现居民自助。在社区各治理主体的充分参与下,X街道打造构建资源平台,加强治理主体的联动效应,充分发挥了各个治理主体的自身优势,探索出属于自身实际的社区协同治理模式,极大改善了社区治理面貌。
猜你喜欢社工居民主体青春社工草原歌声(2021年4期)2021-11-19石器时代的居民阅读与作文(小学高年级版)(2021年6期)2021-09-10论自然人破产法的适用主体南大法学(2021年3期)2021-08-13技术创新体系的5个主体中国自行车(2018年9期)2018-10-13关于遗产保护主体的思考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16年2期)2016-05-17此“社工”非彼“社工”——对社区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概念的澄清大社会(2016年6期)2016-05-04怀旧风劲吹,80、90后成怀旧消费主体金色年华(2016年13期)2016-02-28医务社工的昨天和今天中国卫生(2015年3期)2015-11-19处境尴尬的医务社工中国卫生(2014年10期)2014-11-12高台居民读者(乡土人文版)(2013年12期)2013-05-03